
同性恋是艾伦·霍林赫斯特大多数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他也是首位凭借同性恋题材的作品获得布克奖的小说奖。
小说家艾伦·霍林赫斯特(Alan Hollinghurst)可以称得上是现代英国同性恋文学的吟游诗人。他在1987年发表了处女作《泳池图书馆》(The Swimming Pool Library),故事主人公是个年轻的同性恋贵族,受邀给一位年长的同性恋贵族撰写传记。故事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数年,当时同性恋还被判定为违法,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霍林赫斯特的第二部作品名为《折叠的星星》(The Folding Star),讲述的是一个在佛兰德斯任教的英国人与他17岁的学生坠入爱河的故事,《纽约书评》形容该书是“同性恋版的洛丽塔”。另一部代表作《美丽曲线》(The Line of Beauty)则使霍林赫斯特在2004年获得了布克奖,还被改编为BBC连续剧。该书行文起点正是《泳池图书馆》故事落幕的终点,一个名叫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年轻学者来到伦敦。全书文字优美,叙事风趣,当主人公在舞池中邀请铁娘子玛格丽特·撒切尔共舞一曲时,故事达到了高潮。
霍林赫斯特一直关注着同性恋题材与横亘代际的故事,他最新创作的小说《斯巴尔肖特情事》(The Sparsholt Affair),追踪记录了跨越七十年里多位主人公(绝大多数是男性同性恋者)的人生。故事开始于1940年的牛津大学(霍林赫斯特大部分小说故事的发生地,也是他的母校)。战争阴云笼罩在校园上空,一群学生透过玻璃窗看到一个正在举重的美少年,这个名为大卫·斯巴尔肖特(David Sparsholt)的工程专业学生正在为参加英国皇家空军做准备。虽然他的姓氏成为小说标题的一部分,但我们却从未真正了解过他。几乎就像被迷住的同伴给他画的粉笔肖像一样神秘莫测,画中的他有着完美躯干,但颈部以上空无一物,宛如花萼。
随后,小说便跳转到了1966年,出现了大卫13岁的儿子约翰尼(Johnny)。斯巴尔肖特家族正和另一家人在康沃尔享受海滩度假,也正是在此处发生了本书所谓的“情事”。我们从没明白这件情事丑闻真正蕴意为何,只知道涉及人物包括大卫、一名保守党议员,和一个肯定是同性恋的男妓。霍林赫斯特透露的另一个细节,是一幅透过窗户拍摄的模糊不清的画报照片,和该书开头对学生时代大卫的介绍方式有着悲剧性的共鸣。后面的文章里,霍林赫斯特跳到了1974年、1982年、1995年和2012年,描绘了当年的风流韵事如何在几代斯巴尔肖特人中间回响反射。故事主要叙述了约翰尼的生平,他如今已公开同性恋身份,成为了广受欢迎的肖像画家,一生都与大卫在牛津校园时代的首席爱慕者纠缠不息。
无论对记者还是小说家而言,性丑闻都是极好的创作素材,但没有人像英国人那样“犯案”。有时,是不露感情的沉着和保守,有时,则在意乱情迷时被抓个现行。就像1994年因自慰性窒息死去的保守党议员,被警方发现时全身只穿着一双袜子和吊裤带,脖子上缠绕着电线,嘴中被橘子皮堵满。“我认为,我想要叙述的不只是一桩性丑闻的细枝末节,尤其是带有同性恋元素的丑闻,更想关注丑闻对于涉事人物乃至家人的影响,”霍林赫斯特近期住在多伦多一家酒店里,他在电话里这样告诉我,“在那个年代进入公众视野的同性恋事宜,都被框进了丑闻的范围。这本书里‘情事’就发生在同性恋合法化的一年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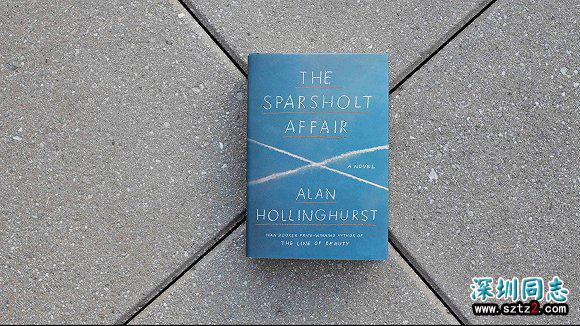
[英]艾伦·霍林赫斯特 著
为深入调查,霍林赫斯特研究了英国最出名的两起性丑闻。首先是发生于1961年的普罗富莫事件(Profumo Affair),该丑闻以事件主角、时任战争大臣的约翰·普罗富莫(John Profumo)命名,他与年轻貌美的模特克莉丝汀·基勒(Christine Keeler)发生婚外情的同时,还跟一位苏联驻伦敦的海军官员有染。1960年代初期的伦敦政局正摇摆不定,该事件的发生最终导致了保守党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的下台。小说家大卫·普罗富莫(David Profumo)是前内阁成员约翰·普罗富莫的独子,霍林赫斯特曾夸赞他撰写了“非常优秀的回忆录”,“他采取了十分聪明的做法,为自己的父母以及婚外恋丑闻之前两人的婚姻关系描绘了一幅精妙肖像,尝试着探索丑闻对学童时代尚不知发生何事,却被带离学校的自己产生了何种影响。”
另一起对霍林赫斯特产生启发的政治丑闻则来自杰瑞米·索普(Jeremy Thorpe),他是口才出众、劲头十足的英国自由党前领导人。1975年,索普被指控因为前任同性恋人威胁要向社会公开他们曾经的伴侣关系,而指派一名空军去刺杀他。但在巨蟒剧团的演出场景里,这个准刺客搞砸了差事,误将前任的大丹狗击毙。既然索普的这桩奇闻至今还能被完整记得,必然也是英式怪癖编年史中颇为奇特的一章。今年晚些时候,BBC将上映由该事件改编的三集迷你剧《英国式丑闻》(A Very English Scandal),由休·格兰特(Hugh Grant)饰演索普,本·威肖(Ben Whishaw)饰演他的前任。
索普既低俗又悲情的倒台,也对同时代的男同性恋者产生了深远影响。且不说他的狂妄自大,如果他是异性恋者,或丑闻发生之时同性恋并不违法,他就不会急着除掉那位前任。这个英国最具潜力之一的政治家衰落之际,1954年出生的霍林赫斯特正在牛津大学研读文学。索普的政治生涯从此一蹶不振,80来岁患上了帕金森综合征,直至2014年去世,基本都是隐居状态。霍林赫斯特谈到:“我对他丧失行动能力的晚年生活略知一二。”
这起真实的同性恋政治丑闻发生的时间,与霍林赫斯特小说设定的背景差不多,为了更好地理解相关细节,作者又参考了一本最近出版的索普个人传记。但他尽力避免在创作小说时背负上历史调查的压力。
“我通常会避开调查,”他说道,“你应该确保创作时期的历史背景无误,但之后就得抛开那些搜集的资料。要把过去展现得像现在一般自然,而不能堆砌太多历史细节。”
霍林赫斯特在撰写小说时,总会遍寻个人经历作为素材。“我常常回味自己二十来岁初到伦敦的时光,”他回忆道,“享受第一次探索同性恋事件时的哑口无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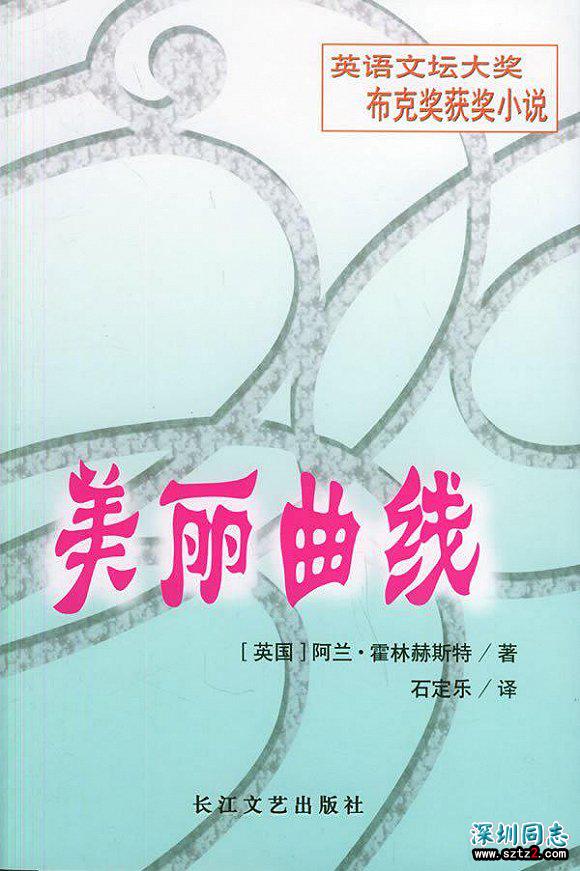
[英]阿兰·霍林赫斯特 著 石定乐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6年
创作《美丽曲线》时,霍林赫斯特并不了解撒切尔夫人支持者群体中的同性恋数据,所以他参阅了一位内阁大臣的回忆录,以及同时期其他第一人称叙述政治生活的文本。比如,《斯巴尔肖特情事》里有关战争时期牛津大学的部分,就来自一位“当时在牛津就读,去年突然去世的老朋友”,他帮助回忆了该时期的真实情景。这位朋友曾接受过艾德蒙·白伦敦(Edmund Blunden)的军训指导,后者是英国两战期间最卓越的诗人之一,也是绝不可轻易放弃的精彩细节(白伦敦曾在《斯巴尔肖特》中有过短暂露面,被提到他在牛津校园训练学生的事情)。霍林赫斯特说道:“我被战争时期的牛津深深吸引,这是一段鲜有人知,也很少有人写到的奇特岁月,很多东西都从伦敦疏散到了牛津校园里,正常情况下的三年学制在服兵役要求出台前被缩减至一年。”他的作品经常被拿来跟伊夫林·沃(Evelyn Waugh)比较,而他本人则希望为读者描绘出德国空军疯狂轰炸英国之时,“牛津校园宛如庄园的模样。”
霍林赫斯特显然也很欣赏如今社会文化对同性恋越来越高的接受度,但在他看来,性向自由化也使得当前时代不再能为小说家提供那么刺激的素材,至少因性向和隐匿相互作用而诞生的题材变得少见了。“我总被拉回早年时光,事情更加复杂,小说家有更丰富的‘谷物食材’,”他说道,“现在,我们没有像过去那么多的丑闻了,让人‘震惊’的门槛也陡然降低。我们几乎对公众生活低俗粗野的一面麻木不仁。”
曾经的同性恋者生活在自己本性被视作禁忌的社会里,大部分人都养成了高度敏感的洞察力和伪装力,同时代的异性恋者并不需要如此。辨别另一位同性恋者的能力被戏称作“同志雷达”(gaydar),甚至比询问别人是否为“多萝西之友”(friend of Dorothy,委婉询问性取向的说法)更重要。霍林赫斯特身为作家的才能多多少少得益于此,他小说里的很多人物也具备这种能力。
《斯巴尔肖特情事》去年在英国出版的时候,距离《泳池图书馆》面世正好30年。“(当时)英国基本没有以正面认可的态度来明确探讨同性恋生活的严肃小说,作为一个小说家,我在这里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绝佳位置,”霍林赫斯特回忆起他的处女作。他作品的独创性很快吸引了很多关注,大部分是积极肯定的。“这让很多人欣喜,也让很多人心烦,有人认为这毫无来由、无法接受,也有人将其放在人类学高度上加以研究。”
霍林赫斯特曾经被视作专门创作“同性恋文学”的“同性恋小说家”,获得布克奖,让他得以终结这种边缘化、少数化的定义。阅读、喜爱他文字的读者里,既有同性恋,也有异性恋。“我把同性恋相关的问题作为创作基础,同性恋者也并非将一生都耗费在性取向相关的问题上。”文学评论家和作家同行普遍认可他是在世最伟大的英国散文化小说家之一。“我觉得,作为一种流派的同性恋文学,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溶解到其他事情的背后了,”他对自己的成就十分谦逊,“这一流派之所以兴起,是响应了新机遇和新挑战,在上世纪80、90年代显得迫切而又必需,现如今已经不再有那么强烈的必要了。”
《斯巴尔肖特情事》打上了作者的深深烙印,随着年龄渐长,他展现出更多幽默,以及,伴随岁月流逝才会产生的挽歌式的视野。霍林赫斯特发出了那个时代“同性恋的声音”。该书最有趣的一幕在临近结尾处,刚刚丧偶的六十来岁的约翰没能抵住约会软件的诱惑,和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在床上缠绵。智能手机上提示着千禧年已经到来,比起身边躺着的真实的、鲜活的、呼吸着的躯体,约翰似乎对那些无头的裸体躯干照片(暗示着几十年前大卫·斯巴尔肖特的粉笔画)更感兴趣。他的表现说明,如今男同性恋者所处境地已经大大改变,当年父辈因为性取向不得不冒着犯法的风险,现在却可以安然乐在其中,“潜在的性爱火花甚至比性本身更加诱人。”
正如《斯巴尔肖特情事》和他的其他作品所证明的,同性恋人生为小说家提供了一张广阔无边的画布,因为这是种“始终变化着的东西”。当我问他现在的约会软件对同性恋文化有何影响时,霍林赫斯特惋惜大部分同性恋者都选择利用智能手机匿名的便利性结交伴侣,使得“很多同性恋专属的空间和地方都消失了”,这种分散还削弱了同性恋酒吧建立起来的社区凝聚感。但与此同时,他也不愿将过去过度浪漫化。“你本可以坐在家里做些其他有意义的事,却只能整晚站在酒吧里端着酒杯搜寻同伴,这其实也挺苦涩的。”







































